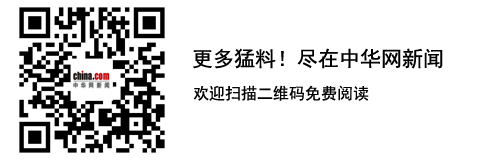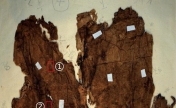第二天,所有晚报上都登了一则简短的讣告,宣布这位忠于职守的军官——雷德尔上校突然死亡。但是,在追查雷德尔案件的过程中牵扯到许多人,致使这件事无法保密,人们也逐渐了解到这件事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揭开了雷德尔的心理活动。雷德尔上校是个同性恋者,他的上司和同事竟无一人知道。他落在勒索者手中已有多年,这些勒索者最后逼他走上这条绝路。现在,奥地利军队一片哗然。大家都明白,一旦发生战争,他一个人就能断送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奥匈帝国也由于他而陷入崩溃的边缘。直到这步田地,我们奥地利人才明白,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已经到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
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
这件事使我第一次感到战争的恐惧。第二天,我偶然遇到贝尔塔·冯·苏特纳,她是我们时代卓越的、大度的卡珊德拉。她出身于名门豪贵之家,青少年时代在自己的故乡波希米亚的城堡的附近目睹过一八六六年战争的惨状。她抱着佛罗伦萨夜莺般的热情,认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就是防止第二次战争,甚至是完全杜绝战争。她写了一部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放下武器》;她组织过无数次和平主义的集会。她一生中最大的功绩是唤醒了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良知,促使他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以弥补他发明炸药所造成的损害。当时她非常激动地向我冲过来,在大街上就高声嚷嚷,而她平时说话是很安静、亲切的。她说:“怎么现在人们还不明白刚发生的事,战争已经开始。那些人再一次在我们面前掩盖真相,对我们保密。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行动起来?这些事与你们的关系最大!站起来去抵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不能什么都让我们几个老太婆来干,没有人会听老太婆的话。”我对她说,我就要去巴黎。也许我们真的会发表一份联合宣言。“为什么说也许呢?”她急促地说,“形势比以前坏多了,战争机器已经在运转。”虽然我已心神不定,但我还是尽力来安慰她。

贝尔塔·冯·苏特纳旧照。
在法国,我遇到的第二件生活小事不由得使我想起那个老太太的预见是多么准确,她看到了未来。可是在维也纳,人们很少认真对待她的话。那是一件特别小的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一四年春,我和一位女友从巴黎前往都兰,准备在那里小住几日,为的是要凭吊达·芬奇的陵墓。我们沿着卢瓦尔河散步,春风和煦,我们贪图欣赏春色,晚上回到住处时,两腿似铅重。于是,我们决定到十分安静的图尔城去看电影,过去,我曾在那里拜访过巴尔扎克的故居。
这是郊区小城的一家电影院,它不能与用闪光金属板和玻璃装饰起来的现代化豪华电影院相提并论,只是凑合修起来的一间大厅,里面挤满了各类小人物:工人、士兵、市场上的女商贩,他们是一些真正的老百姓。他们无拘无束地闲聊,同时向污浊的空气中喷着斯卡费拉蒂牌和卡波拉尔牌低劣香烟的蓝色烟雾,尽管室内挂着“禁止吸烟”的标牌。银幕上开始放映《世界要闻》,先是英国的划船比赛,观众照常闲扯和抽烟;接着银幕上出现了法国的阅兵式,人们仍没有注意;随后是第三个画面:威廉皇帝到维也纳拜会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银幕上,我看到了熟悉的维也纳西车站冷冰冰的站台,站台上站着一些警察,正在等候进站的列车。接着出现的是年迈的皇帝沿着仪仗队走过去,准备迎接他的贵宾。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有点驼背,步履艰难。图尔人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出现在银幕上时,他们善意地发出笑声。接着是列车进站的画面,第一节车厢,第二节车厢,第三节车厢。沙龙式的豪华车厢打开了,威廉皇帝从中走出来,翘着高高的八字胡,穿一身奥地利的将军服。

纪录片《启示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剧照。
威廉皇帝在银幕上刚一出现,昏暗的大厅里立刻爆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口哨声和跺脚声,他们完全是自发地大喊大叫吹口哨;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们,无不发出嘲笑,好像画面上的人侮辱了他们似的。善良的图尔人除了报上登的消息外,并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刚看到威廉皇帝,就像发了疯似的——我感到十分吃惊,不由得惊恐万状。我觉得,经过多年对德国仇恨的宣传,流毒已浸入平民百姓的心里。在这个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这里的市民和士兵毫无恶意,却对威廉皇帝、对德国有这么大的仇恨。银幕上不过是一闪而过的画面,就引起这么一场骚动,只不过是一秒钟,仅仅一秒钟,可见流毒是多么深广。下面继续放映其他画面时,他们就把刚才的一切忘记了。当晚放映的主片是一部喜剧,观众看得前仰后合,笑个不停,有人乐得把大腿拍得啪啪直响。那仅仅是一秒钟,而那一秒钟却被我看到了。我们曾做出过不少努力,想方设法促进国家间和民族间的谅解。可是到了关键时期,彼此双方的人民是多么容易被煽动起来啊!
那个晚上我心灰意冷,一夜未眠。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巴黎,虽然我同样会感到不安,但不会这么激动。我觉得十分可怕的是,仇恨的心理已深入外省,深入到善良质朴的平民百姓中间。几天后,我同朋友们讲起这件事,但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怎么严重,他们说:“我们法国人过去也嘲笑过肥胖的维多利亚女王,但两年以后,我们与英国结成了联盟。你不了解法国人,法国人对政治从来不往心里去。”只有罗曼·罗兰的看法不一样,他说:“百姓越老实,就越容易轻信。自从彭加勒当选以来,形势一直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并不愉快。”我们长时间地讨论起夏天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不过,对这次代表大会,罗曼·罗兰比其他人更持怀疑态度。他说:“一旦发布动员令,到底有多少人能坚持得住,谁能知道?我们已陷入一个群情振奋、歇斯底里的时代,在战争中绝不能忽视这股歇斯底里的力量。”

罗曼·罗兰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