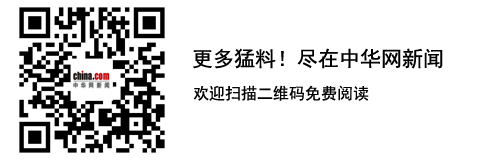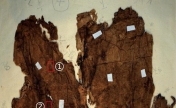自工作时间缩短以来,无产阶级的生活开始好起来,至少有一部分家庭已过上小康生活。到处都在进步,谁敢于大胆作为,谁就能获得成功。谁买上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旧书或一张名画,就会看到行情不断上涨。谁越大胆,越舍得出本钱办一家企业,谁就越能保证赚到钱。无忧无虑的美妙景象笼罩着整个世界,有什么能打破这种景象呢?又有谁能阻止这种从自己的热情中迸发出来的干劲呢?欧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富裕和美丽过;欧洲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除了少数老态龙钟的老朽,没有人对“美好的旧时代”依恋不舍。
除了最贫困的人以外,星期天没有人待在家里。所有的青年人都出去徒步漫游,爬山和比赛,同时也学习各种体育项目。假期里,人们都出门远游。不像我们父辈那个时候,放了假只到离城不远的地方,最多到萨尔茨卡默古特去。现在的人们对整个世界都感兴趣,想看看世界上是否处处都那么美,是否还有更美的地方。过去,只有那些有特权的人才能到外国去旅游;而现在,银行职员和小业主都有条件到法国、意大利去旅游。现在出国旅游比过去便宜多了,也方便多了。主要是人的观念起了变化:有新的勇气,有新的敢闯精神,出去旅游才更大胆;在生活上节俭和谨小慎微是丢人的。这代人决心使自己成为更富有青春活力的一代人。每个人都为自己年轻而感到自豪,这一点与父辈们正相反;首先是年轻人脸上的胡子突然没有了,然后是那些年龄大的人去仿效他们,为的是不显出自己老相。年轻、精神焕发已成为当时的口号,人们不再老成持重。妇女们甩掉了束胸紧身衣,再也不打阳伞和戴面纱,因为她们不再害怕空气和太阳。她们把裙子裁短,便于打网球时两腿跑动;她们露出丰润的部位时,再也不感到害羞。风尚变得越来越合乎自然。男人穿着马裤;女人敢于坐在男式马鞍上,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再有什么需要遮掩和隐藏的。世界不但变得更美丽,也变得更自由了。

英剧《唐顿庄园》(第一季)剧照。
在我们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在习俗方面也赢得了这种自由,他们生活得健康又充满自信。人们第一次看到,年轻姑娘在没有家庭女教师的陪伴下,独自同男朋友一起运动,一起郊游,他们完全是一种公开的、自主的伙伴关系。她们既不害羞也不矫揉作态。她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她们摆脱了父母严厉的监督,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她们当女秘书、女职员,得到了自己安排生活的权利。卖淫——旧世界唯一被允许的色情交易——明显地减少了。由于提倡新的更为健康的自由,男女之间假正经的行为早已成为背时的东西。从前在游泳池里隔开男女的木板,现在陆续被拆除。男女不再忌讳,他们知道彼此长得怎样,也懂得人类繁衍的秘密。在这十年里重新获得的自由、大方和自然,胜过以往的一百年。
现在世界上有了另一种节奏。一年里发生的事胜于过去的几倍,几十倍!一项发明紧接着一项发明,一个发现紧接着一个发现;每个发明和发现都以飞快的速度变成人类共同的财富。因此,每个国家都第一次感觉到彼此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在齐柏林飞艇初次航行的那一天,我正在前往比利时的途中,恰巧在斯特拉斯堡停留。我在这里亲眼看到了飞艇在大教堂上空盘旋,下面的人们热烈地对着飞艇欢呼,盘旋的飞艇好似在向这座有千年历史的教堂频频点头。晚上,我在比利时维尔哈伦家得到消息,飞艇已在艾希特丁根坠毁。维尔哈伦满含泪水,激动万分。如果他仅仅是作为比利时人,那么他对这次德国的空难就会抱无所谓的态度,但他是欧洲人,又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所以他会和我们一起分享战胜自然的共同胜利,也会同我们一起分担我们共同遭受的考验。当布莱里奥驾驶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时,我们在维也纳欢呼雀跃,好像他是我们国家的英雄。大家都为科学技术取得如此迅速的进步而感到自豪。现在我们的感觉是欧洲是一个共同体;欧洲意识是我们正在形成的共同意识,我心里想,如果一架飞机能够轻易地飞越国界,那么国界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些海关关卡和边防岗哨就成了无用的摆设,与我们的时代精神是相悖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热切地期望着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共同实现大同世界。这种感情的高涨像飞机的腾飞一样美妙无比。
有些年轻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欧洲各国之间相互信任的那最后几年,我今天仍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我们周围的空气不是死的,也不是真空,空气本身就携带着时代的繁荣和脉搏。空气会不知不觉地将时代脉搏传入我们的血液和内心深处,传入我们的大脑,并不断地传到每一个人。在那几年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从时代的普遍繁荣中吸取了力量。由于大家都有这种信心,那么个人的信心也就大大增强了。也许我们像今天的人一样,当时并不知道那股将我们卷入其中的浪潮有多大,有多少风险。——可是,事与愿违。只有经历过那个对世界充满信心时代的人,今天才会明白,从那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倒退和黑暗。
当时的世界无比壮丽美妙,就像服了滋补药似的浑身是力量。这股力量从欧洲的各条海岸线敲打着我们的心脏。可是我们却没有预料到,使我们深感幸运的事同时也潜藏着危险,当时席卷欧洲的自豪和信心风暴,本身就带着乌云。也许繁荣来得太快了,也许欧洲各国和各城市强大得太急促了,所以那种浑身是劲的感觉总是诱发个人和国家去使用甚至滥用自己的力量。法国的财富充裕,但是它贪得无厌,它还想要一块殖民地,尽管法国的人口已不足以维持殖民地的统治,可它还想侵略,差一点同摩洛哥动武。意大利觊觎着昔兰尼加。奥地利要吞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把矛头指向土耳其。目前德国暂时被排斥在外,但它的利爪总想伸出去,大抓一把。欧洲各国的头脑里都充满了蠢蠢欲动的热血。这些国家扩张的野心到处膨胀,像流行病那样传染,但同时也要有效地巩固国内的秩序。那些发了大财的法国工业家唆使同样肥胖的德国工业家,两家大公司联手合作。——克虏伯公司和法国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都要推销更多的大炮。拥有巨额股票的汉堡海运界和南安普敦海运界对着干。匈牙利农场主和塞尔维亚农场主对着干;这一帮康采恩反对另一帮康采恩。经济的暂时繁荣使所有人像发了疯似的,拼命攫取更大的财富。
低估和忽视了危险
如今,当我们心平气和地问自己,一九一四年欧洲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我们找不出任何充足的理由,也找不出它的诱因;这次战争不是出于思想上的纠纷,也不是为了争夺边境的几个小地方。我认为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战前四十年和平时期积聚起的内部力量,它必然要发泄出来。每个国家都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想要使自己强大的情感,可恰恰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这种情感。每个国家想从别国得到更多的财富,可是这些国家也想从别国得到财富。而最糟糕的是,我们被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欺骗了,那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每个国家都想让别的国家在最后一分钟被吓退,于是外交官们就利用起恫吓的手段,一次又一次,四次、五次在阿加迪尔,在巴尔干战争中,在阿尔巴尼亚,都玩弄起这种手段。巨大的同盟国之间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军事化。和平时期德国就征收战争税,法国延长了服役期。多余的力量必然要发泄出来。巴尔干的爆炸信号则显示出,战争的乌云已向欧洲靠近。

英剧《唐顿庄园》(第二季)剧照。
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惊慌,但是有一种不安始终郁结在心头。每当从巴尔干传来枪炮声,我们总有一点点不安。难道战争果真会落到我们头上?我们并不知道战争的起因,也不知道它的目的。反对战争的力量集合得太慢了,如我们所知道的,集合得太慢了,太畏首畏尾了。反对战争的力量中有社会党和数百万宣称不要战争的人——对立的双方都有这样的人,有教皇领导下的天主教组织,还有若干跨国的康采恩,另外还有少数几个反对国家统治者搞秘密交易的明智的政治家。我们这些作家也站在反战的一边,诚然,我们这些人一直是孤立地工作,单枪匹马,而不是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很遗憾,知识分子通常抱漠不关心的消极态度。由于我们的乐观主义,我们在思想上不会预见到战争的来临,根本不会去想战争带来的各种道义上的后果。当时社会名流写的重要文章,没有一人提到过战争问题,或者大声疾呼去告诫人们警惕战争。当我们以欧洲的思维方式来考虑,在世界的范围内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当我们在自己的范围内——对于时局我们只发挥间接作用——认清这样的思想:不分语言和国别,以和平的明智态度增进谅解和加强思想上的团结,我们认为这就足够了。并且,恰恰是新的一代对这样的欧洲思想最为拥戴。我在巴黎曾看到一群年轻人团结在我的朋友巴扎尔热特周围;他们和老一辈不同,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好侵略的帝国主义。
儒勒·罗曼、乔治·杜阿梅尔、夏尔·维尔德拉克、杜尔丹、热内·阿科斯、让·理查德·布洛克等人先组织了“修道院”文社,然而变为“争取自由”文社。他们是一群热情的先驱战士,他们正在迎接欧洲主义的到来。欧洲刚刚露出战争的苗头,他们就无比憎恨地反对任何国家的军国主义。法国过去很少产生这样一群勇敢、坚定、有才华有道德的年轻人。在德国,魏尔菲和他的“世界朋友”雷内·席克勒一起为促进谅解而热情地工作着;雷内·席克勒身为阿尔萨斯人,命中注定要介于两个国家之间,他在感情上特别强调,世界各族人民要和睦相处。作为我们的同志从意大利向我们发来问候的是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盖塞。从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各国也不断传来鼓励。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写信给我:“还是到我们这里来吧!让那些煽动我们进行战争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看看,你们这些奥地利人是不要战争的。”是的,我们都热爱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也热爱欧洲!我们坚信理智将会在最后时刻阻止那种错误的游戏。我们过分相信理智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错误。当然,我们没有抱着怀疑的态度来观察眼前的征兆,而是充满自信,这不正是青年一代应该有的思想吗?我们坚信,欧洲的精神力量、欧洲的道德力量,将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战胜一切。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在进步中必然产生的乐观主义,使我们低估和忽视了我们共同的危险。

电影《1917》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