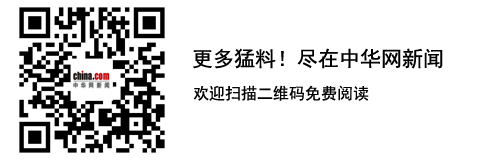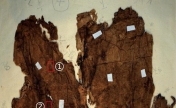一种绝对之虚构——天使,
在你发光的云彩里安静一下,听听
正确的声音那发光的旋律。
——《朝向一个至高虚构的笔记》
这个“绝对之虚构——天使”,无疑是诗人的化身,是它在朝向或者发明了“至高虚构”,它是“事物如其所是”、新秩序得以形成的大前提,它也的确是史蒂文斯所言的“必要的天使”,在它自身的事理内。
史蒂文斯也以略显慷慨陈词的方式为天使的必要性辩护,在《高贵的骑手与词语的声音》一文中,他说到:
事实上,有一个诗歌的世界足以与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或者,我应该说,无疑,与我们将会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相分别,因为令诗人成为他所是,或曾是,或应该是的那个有效的形象的是,他创造了我们不间断地转向而一无所知的世界,以及他赋予生活那些至高的虚构,没有它们,我们就无从想象它。
这是史蒂文斯的底牌,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底牌,但也是一个虚无的底牌,当天使是“必要的”,或许恰恰表征了它的“不必要”。而天使之所以必要,也正是缘于那个意识形态的幻觉,在《徐缓篇》里,史蒂文斯不得不承认,“最终的信仰是信仰一个虚构。你知道除了虚构之外别无他物。知道是一种虚构而你又心甘情愿地信仰它,这是何等微妙的真理。”而这一真理的微妙之处还在于,史蒂文斯预留了一份难得的清醒,“这一天会来临:诗歌一如天堂,看上去就像一个悲凉的装置。”当诗歌试图替补天堂的空缺,也必然会复制天堂的失落,而问题仅仅在于,它这么做或者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一天”已经来临。
史蒂文斯的诗学再一次印证了胡戈·弗里德里希的观点,现代主义诗歌是一种“去浪漫化的浪漫主义”。史蒂文斯虚构那一“必要的天使”,自然内在于这一西方传统,也来自于他所说的“现实的压力”,诸多现代世界的混乱,让史蒂文斯选择了“逃避主义”的诗学。当然,在史蒂文斯“朝向至高虚构”的过程中,他是在他哈特福德的私人花园里,喝酒,品茶,享受着高雅的艺术生活。不管怎么说,“至高虚构”同时是一种“至低现实”,“必要的天使”越说自己与现实无关,就越与现实有关。
在中国,史蒂文斯所代表的国际传统,早已被兑换为或主流或山寨的本土风格,在争相移植和模仿中,“诗”不仅仅是“这首诗的主题”,也是人生的主题,“朝向至高虚构”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当陶醉于史蒂文斯所营造的诗人是“在向一群精英致辞”的优越感时,不妨仔细品味史蒂文斯在《徐缓篇》中的另一句箴言:“要想有独创精神,就必须有外行的勇气。”所谓“外行”,大概就是跳出“虚构”的幻境,回到热闹的现实,天使尽可以虚构,但别让天使虚构了自我和生活。
撰文|娄燕京
编辑|商重明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