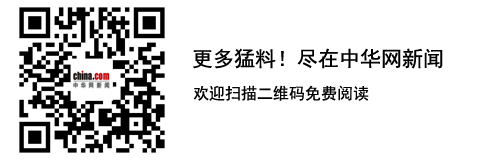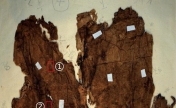如同所有的谄媚都指向权贵。
凡·高成为二十世纪一只最为丰腴和孱弱的羔羊,
它因满足所有人的胃口而沦为公共用品。
他以惊恐的目光注视着那些争先恐后的攫取者。
身无分文的印象派画家又一次惨遭洗劫。
继痛失爱情、尊严和耳朵之后,
他又一次被釜底抽薪,
偷盗者毫不犹豫。
迟来的歹徒有一个冷酷的名字—冷冰川。
这位最后到来的盗匪抢走了画家最宝贵的东西—色彩。

向日葵般沸腾的色彩消失了,只剩下黑白。这两个幸存者醒目地对立着,如同两名最后的极端分子,手持利器,互不妥协。这种尖锐的对立恰巧吻合了世界的真相—所有的色彩,都埋伏于黑白两色之中,仿佛彼此交替的白天与夜晚,将世间一切事物纳于自己统治之下。黑与白,分别被魔鬼与天使征用,它们在各自的版图中分别掌握着最高权力,而那些看上去斑斓华丽的色泽,无不是它们卑微的子民。
大面积的光斑消失之后,我们与凡·高重逢。瘦削的面庞、惊惧的目光、被纱布包裹的耳朵(是耳根),是他永不丢失的证件。我们由此辨识了他的身份。“凡·高”是一个无法冒充的名字—现代社会据说已经进化到可以炮制一切,比如没有父亲的孩子、消失的处女膜以及浑身硬伤的著名学者,唯独无法复制出一个凡·高来。那只跳跃而去的耳朵,象征着某种舍弃和牺牲。当艺术沦为人们纵欲的支票,没有人愿意如此蔑视自己的肉身。雪白的刀刃,划开了凡·高与众人的距离。如果用上现代人最为熟悉的词汇—交易,那么,这或许是由凡·高亲手完成的唯一交割。耳朵是他身上最后一枚金币,他在嘲笑中支付给命运。众声喧哗,在他缺席的耳朵后面,旺盛的向日葵寂静地绽放。
凡·高用画笔表达对世界的看法。狐步舞曲中,上流社会以优雅的姿势欣赏着油画,并认为与画家达成了默契。
凡·高的画在画廊与客厅之间流通,而凡·高本人则往返于漆黑的矿洞和寒冷的棚户。炫目的阳光和诡谲的星辰、不安分的愿望和铁一样沉闷的生活,歌声以及噩梦,在他笔触中,彼此缠绕、冲撞。我们看到大的植物—向日葵、树木、麦田、鸢尾花……看到植物也有神经,在不被察觉的深处呻吟或者呼喊。
一个朋友说,贫穷就像吸毒,也有一种特异的魅力,容易使人上瘾,尤其对于穷人中间那些性格孤僻、儒弱的人。正如一个人在完全绝望时反而获得清醒的神智,非常恶劣的窘迫和贫困同样带给我们异常敏锐的感官。很多年代里,人类对于贫困保持着精细的味觉,这是使人叹为观止的准情神领域。因为贫穷使我们的身心坠向真正的民间。诗人布莱说,贫穷而能听见风声也是美的。
在文明社会之外,凡·高行走在自己的笔触里,贫穷像冬天里的空气一样固执地包围着他,令他无处躲藏。贫穷是甘草和牛粪混杂成的一种健康气味,与沙龙里的芳香大相径庭。凡·高在给提奥的信中表达了一种极为简单的愿望:我要告诉人们一个与我们文明的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一幅农民画散发出火腿味、烟味和土豆热气,那不要紧,绝不会损害健康的;如果一个马厩散发出粪臭,好得很,粪臭本来是属于马厩的;如果田野里有一股成熟的庄稼或土豆或粪肥的气味,那是有益健康的,特别是对城里人。这样的画可能教会他们某些东西。但是,香味并非是一幅农民画所需要的东西。
在凡·高的画前,富人们小心翼翼地戴上雪白的手套。他们感谢上帝,赐给画家贫穷。

很多年后,一个才华横溢的中国画家,在散发着陈旧气息的荷兰街巷与凡·高不期而遇。中国画家内心的黑白底片见证了他的瞬间表情。

他的表情已平静许多,目光由惊惧转为深邃,略近于一八八九年的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