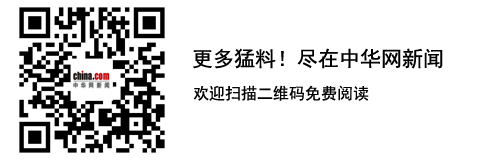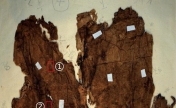如果说,《“是晴天还是阴天?”》的乐观情绪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精神动能,那么,《囚徒》中的自我分裂、对抗与不无悲壮的承担,则闪烁着现代主义悲观色泽。无怪乎后来的研究者强调艾米莉诗歌的重要性时,提醒我们艾米莉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较为中肯的判断来自英国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他在《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一书中,认为“勃朗特姐妹可以被称为晚期浪漫主义作家”,是“转型式人物”。
浓烈的个人情感、壮美的大自然乃至神秘的瞬间幻象,这些因素发而为诗,必然需要借助想象的力量,就如艾米莉提到她能看到幻象时所言,这一切都是由于“热烈想象的滋养”。在题为《致想象》的诗中,艾米莉称“想象”为“我真正的朋友”,因为有它,她不再孤单,能克服对外面的世界的“危险、罪和黑暗谎言”,使她可以加倍珍惜内在的世界,可以“守住一片明亮”,即便“大自然可悲的真相”会“蹂躏践踏”梦想“新开的,幻想的花朵”,但她见过的幻象帮助她确认了那个世界的“真实”,怀着对“想象”的感激,诗人理解到她的责任,同时也是诗歌的功能:“更肯定了人类关怀的慰藉,/更甜蜜了希望,当希望失望的时候”。正是“想象”,这位诗人“真正的朋友”,作为使者,带给我们艾米莉·勃朗特的不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