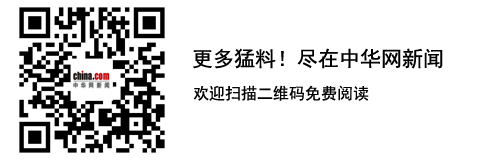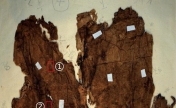为安邦彦所荼毒,残害特惨,人人恨不能洗其穴。
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第势为所压,生死唯命耳。因土司纵容,甚至还有人掠卖人口——
土人时缚行道者,转卖交彝。如壮者可卖三十金,老弱者亦不下十金。
苦难而残酷的贵州大地最终给予他重创——数次遭遇抢劫、诈骗与背叛,徐霞客失去所有盘缠,甚至失去了和他一路同行的僧人朋友。
但是他答应过朋友,要带着他一起登上彼时中国西南的佛教圣地——鸡足山。
于是,他背起朋友的尸骨继续前行,誓要完成朋友的遗愿。
一年后,徐霞客终于得以进入云南,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两次登临鸡足山,撰写《鸡足山志》。
他跨过澜沧江,抵达他旅行的极限——腾冲,又折返北上,远游至云南丽江。
长期行走毁坏了他的双脚,到丽江之后,他已无法行走,但仍在坚持编写游记。1640 年,他病况更加严重,云南地方官用车船送徐霞客回到江阴。
1641 年正月,五十六岁的徐霞客病逝于家中。他的遗作经友人整理成书。
登不必有径,涉不必有津,
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
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
途穷不忧,行误不悔。
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
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
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这是康熙年间徐霞客的江南同乡潘耒为《徐霞客游记》所作的序言。
我在想,是不是有那么一刻,徐霞客的心中也包含着一丝丝的遗憾。当他站在腾冲的云峰山上向更远的南方眺望,却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向那里走去。 这个世界还很大,但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已经用完了。
徐霞客:如果一生只能追寻一种意义,那就是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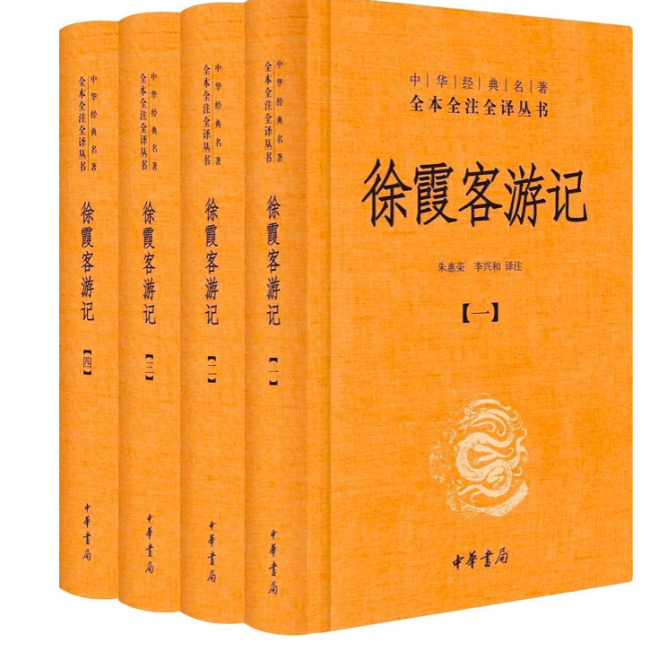
作者: 徐霞客
出版社: 中华书局
译者: 朱惠荣 / 李兴和
出版年: 2015-5
三、他从一开始就和前辈们不一样
明初的周忱写道过,“ 天下山川之胜,好之者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文 ”,认为真正的旅游家必须同时“能至”、“能言”、 “能文”,三者缺一不可。
徐霞客无疑把三者都做到了极致。但这并不是他所以能被人们记住的原因。
在他之前,伟大的旅行家有很多,汉朝的张骞,唐朝的玄奘,宋朝的丘处机,而他,从一开始就和他的前辈们不一样。
在徐霞客之前,中国古代人们旅行主要有几种。
像郦道元写《水经注》,是为官之余的业余工作,可谓不闲不为。
像苏轼一路辗转黄州、惠州、崖州,是被贬谪的不可不为。
像汉武帝巡游天下,是彰显帝王权威的不阔不为。
像盛唐诗人们互相串联,饮酒唱和,遍访名山,是享受型的不乐不为。
像西天取经,是目的性为主导的不用不为。
而徐霞客呢,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介布衣,身处体制之外,不受官方委派,他的旅行是全然自发的,以旅途本身为核心。 他旅行不为修身养性,也不是为了寻找文学灵感,而是把行走本身作为他的灵感。
路途上,他并不循例官僚士大夫的宦游,依照官道就近旅行。为了探究到异样的景致,“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
在水上,他乘坐一叶小舟,在地面上,就几乎全靠步行。遇到仆人逃跑的情况,还要自己背负全部的行李。因为不是官员,他不能投宿驿站,事实上,他也很少住客栈,除了投宿寺庙,一条小船,在白天是他的车马,夜晚就是他的客栈。
他作为时代的普通人,他用这样的方式旅行,却留下了200多万字的游记。所谓“古今纪游第一”,此言不虚。

在科学上,徐霞客是个十足的实证主义者。他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材料,否定了被人们奉为经典的 《禹贡》中一些地理概念的错误,证明了岷江不是长江的源头,辨明了左江、右江、大盈江、澜沧江等许多水道的源流,同时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研究卡斯特地貌的人。
在文学上,他的游记在写作方式上摆脱了“流水账”式刻板的记述,让旅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书写,又进了一步。
对黄山的云海,在游记中,他有非常精彩的描写:
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
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于如臂,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
山高风钜,雾气去来无定。
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峤,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
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徐霞客旅行的关注重点,那就是 强调对旅途本身的叙述。 对动作动词和行动动词的巧妙使用,让词语形成的画面不仅鲜明,而且还有连续的移动感。而徐霞客自己就是这种种场景中的参与者,通过写作, 他重构出运动的场景和此情此景中的身体经验。
用我们更熟悉的概念来说,这是徐霞客的主观叙述。
跟随他足迹与遭遇的变化,能看到他对自己心情和感受诚实的表达。感到他的悲哀、遗憾,快乐与狂喜。 而那种直接的个人经验,正是旅行文学中最吸引人最能共情的地方。

四、生命的意义在于“再次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