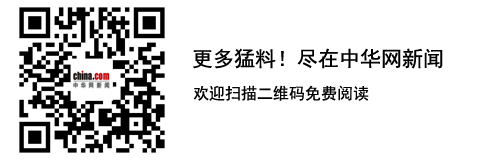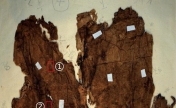走进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很容易被造型特别的展品吸引眼球,虽说是宋瓷,竟然能看到鼎、鬲、琮、樽、觚等先秦时期的古礼器,实在与大众印象里的宋代风物有挺大差别。只不过这些物件并非青铜器,而是精美的瓷制品。在中国瓷器史上,南宋之前,很难见到这些先秦礼器以瓷器的面貌出现。那么后来它们为何会如此集中地涌现于南宋实质上的“都城”临安呢?这与一场倾国离乱——靖康之变相关。而一切的源头,还要追溯到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身上。

官窑灰青釉双耳香炉,南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汴京官窑的迷雾
在我国瓷业发展史上,宋代是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瓷窑遍布大江南北,名窑迭出,瓷器亦品类繁多,各竞风流,并开始对欧洲及南洋诸国大量输出。宋代瓷业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为代表,其中“官窑”最易引起歧义。从字面上来看,广义的官窑泛指历代官府烧造瓷器,贡器或者官场皆可作此称。但在瓷器史上留下浓墨重彩、跻身五大名窑之一的那个官窑则是特指宋代由宫廷所设,为皇家烧制瓷器的窑场。南宋以后,“官窑”成了特定的专有名词,后世历代皇家所设窑场所烧制的瓷器则以“御窑瓷”代称。
官窑有北宋与南宋之分,其中北宋官窑存在巨大争议,连设窑的时间、地址本身也有不少谜团。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北宋官窑的遗址;二是北宋官窑存世的瓷器极其稀少,仅有的几件还是存疑状态。学界甚至有较激进的一种观点,认为北宋官窑压根就不存在。但是北宋官窑的确有明文记载,南宋文人顾文荐在《负喧杂录》里记载:“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另有叶寘于《垣斋笔衡》中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宣政”宋徽宗的两个年号“宣和”与“政和”,也就是说官窑出现于北宋末年。顾文荐和叶寘都生活在距离宋徽宗时代不远的南宋,他们的记载应是较为可信的。但为什么即使有文献还会存在争议呢?

青瓷三登方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迄今为止,仅在传世品中发现过汴京官窑出产的青瓷,造型古雅,釉色莹润,为世间所珍。这就引出一个争议问题:假如北宋官窑的确存在,那么所烧产品唯供朝廷使用,不在市场流通,罕珍和稀有,常人难以见到,更遑论民间收藏,这些传世的珍品如何准确溯源?很难。假如汴京官窑只提出了计划而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那么所谓北宋官窑瓷器是否有可能是受官方委托民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器物?似乎也说得过去。有学者认为,北宋官窑不存在,仅有的几件传世北宋官窑器应是汝官窑。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不妨从具体器物来分析,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官窑弦纹瓶杯是代表文物之一,它最具特色之处在于仿汉代铜器式样,器身布满大片纹,纵横交错,线条简洁雅致,凸起的弦纹增强了器物的装饰性,釉色则给人凝厚深沉的玉质美感。这种仿制古青铜器物与后来南宋官窑器的特点很一致。而且北宋官窑的釉色、胎质都与官汝窑不同,釉层较薄,并有“紫口铁足”,只有在裹足支烧这个特点与汝窑相似。
当然,只凭器物推测依然很难定论,要知道没有在窑址出土的东西,即使有古代大咖的认证,也难以成为铁案。最典型的例子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粉青三登方壶,这件文物是清宫旧藏,早年被定义为北宋官窑所制,最关键的依据就在三登方壶足内面刻有乾隆皇帝御制诗《咏官窑三登瓶 》:“修内成秘器,年陈陶气澄。那馀下策火,祗裂细文冰。葆有精神足,疵无髺垦曾。耤回閒玩古,即物祝三登。”诗末署“乾隆甲午季春(1774)御题”。作为皇家旧藏,又有乾隆皇帝御笔认证,理论上很有说服力了。但这件文物依然引起了专业人士争议,有观点认为此物是清代宫廷的仿制品,并不属于北宋时期。也有观点认为三登方壶是明宣德时期的器物,因做工精致,仿真度高,就连“大收藏家”乾隆帝也把它当作北宋官窑的器物。这些观点你来我往,各有各的道理,最后搞得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拿不准了,于是近年又将原先定义粉青三登方壶年代的“北宋”标签拿掉。
为何北宋官窑处境如此尴尬。这就涉及瓷器文物鉴定的硬性标准——窑址物才是确定瓷器是否真品最关键的证据。遗憾的是,现在存世的北宋官窑文物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根据文献记载推测,北宋官窑地点设在汴京附近,即今天河南开封市。宋代以后,这座位于黄河之滨的城市被洪水淹没多达6次,尤其是明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的起义军攻打开封时,交战双方都试图采用水攻,决口黄河,结果导致开封全城毁灭,许多建筑随之全部淹没于地下。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是导致北宋官窑遗址沉底、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的重要原因,加上没有充足的文献资料支撑,北宋官窑的谜团很难在短期内解开。
瓷的礼器功能开始彰显
“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是元末明初收藏大咖曹昭对官窑瓷器特点的描述。遗址发现前,出自官窑的存世品非常稀少,却是宋代五大名窑里规格最高者。官窑制品普遍施有乳浊性厚釉,口沿处釉层较薄,泛出比黑胎稍浅的紫色;底足无釉处则呈现胎的颜色;瓷器上口沿薄釉处露出灰黑泛紫,足部无釉处呈现铁褐色,即所谓的“紫口铁足”。虽然这种特征在哥窑和龙泉窑烧制的瓷器身上也能看到,只是官窑制品釉面更为沉重幽亮,釉厚如堆脂,温润如玉。同时,釉面多层反复细刮,纹理布局规则有致,规整对称,颇有宫廷气势。

官窑青瓷盏,南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
官窑器物之所以细致精美,在于有朝廷埋单,可以不计工本、力求完美。但南宋官窑最明显的特点绝不是做工,而是器型。根据窑址出土瓷片经修复后的作品来看,日用品不是主流,更多的是仿古时铜器、玉器等礼器而制成的瓷器。较为典型的有官窑青瓷簋式炉,其形制仿商周青铜簋式样,不过到了宋代,这类器物的功用不再是商周时期用来盛食物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香炉的样式,主要作为礼器使用;同样情况的还有官窑鼎式炉,先秦时期,鼎不仅仅是用来烹煮食物,也是放在宗庙里祭祀用的一种礼器,对“崇古”的宋人来说,鼎也可以作为供香的香炉;官窑觚更是给人一种古物新生的既视感,作为盛行于商周时期的酒器,觚在宋代已经是十分遥远的存在,但南宋官窑却用另一种方式让它重现人间,不再以青铜铸造,而是釉色粉青、胎骨灰黑的瓷觚。不知千年前的孔夫子看见这一瓷觚,会不会也有“觚不觚”之叹。此外,仿古青铜器而制的作品还有官窑樽式炉、鬲式炉、琮式瓶等等,甚至可以说南宋官窑的瓷制古礼器不仅是宋代复古之风最直接的反映,也是中国瓷器史上具有划时代标志的创造。

官窑青瓷簋,南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所以,为什么南宋官窑里会出现这么多仿古青铜礼器或古玉礼器的器型?很大程度取决于时代背景。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历朝皇家向来注重祭祀,一年之中祭天、祭地、祭社稷、祭郊坛、祭宗庙等大型祭祀是少不了的,此外还有各种中、小祭祀活动,宋代也不例外。古时候的礼器主要以青铜、玉为材质制作,陶瓷主要还是制作生活用品,即使到瓷业已非常发达的北宋,依然是日用品瓷器占主导地位。在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影响下,宋朝皇室也兴起复古之风,宋徽宗个人对瓷的青睐让瓷器地位迅速提升,加上这位“青铜”皇帝在宫中收藏了大量古董礼器并编撰成书,这些客观因素都极大解决了官窑烧制仿古礼器时的技术难题,也是其他民窑不具备的条件。

官窑青瓷弦纹贯耳壶,南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但真正让瓷制品登上国之礼器尊位的,是一场国难。靖康之变,北宋覆亡,宫中礼器多佚失。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应天府,改年号为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个皇帝,即宋高宗。南渡后宋高宗自然需要把皇家的面子重新撑起来。建炎二年(1128),尚未摆脱亡国危机的宋高宗刚到扬州就设立郊坛开始祭祀,但当时大家都是逃难而来,哪有礼器举行祭祀?于是高宗向还滞留在汴京的官员发出号召,让他们南渡时带着礼器,可见当时宋室礼器匮乏。不料第二年金兵继续南犯,高宗仓皇南逃,那些好不容易从汴梁带出来的礼器又在途中“尽皆散失”。所以南宋从建立之时起,皇室就面临缺礼器的困境,加上偏安江南,国力未实,要想使祭祀延续,就不得不权变。南宋地方志《咸淳临安志·郊庙》有段关键的记载:
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
意思说得很明白,祭祀是国家大事,规格不能偏废,只是所用礼器本应用铜、玉制成,当下没有这个条件,咱就先用陶瓷、木头制作的替代。帝王出驾时仪仗队的旗帜本来应该用华丽且珍贵的文绣布料制作,现在也因陋就简,用有花纹的丝织品替代也成。
面对如此海量的祭器需求,自然得设窑场进行烧制,起初南宋朝廷采用的是“官搭民窑”的方法,与地方大窑合作,先后在绍兴府余姚县、平江府等地的窑场下单,令他们烧制宫廷祭器。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余姚和平江的窑场也算得上是南宋官窑的前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已在宁波慈溪市的低岭头发现“余姚官窑”窑址,此地南宋时属于绍兴府余姚县的,很可能就是当时为宫里烧制礼器的窑场。到绍兴十三年(1143)后,由于宋高宗对余姚县和平江府两地所生产的祭器始终不满,索性决定自己办窑场,专款专用,于是先后设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这两个窑口因是皇家专设,烧制标准、规格也比较高,从这里出来的祭器也总算得到了宋高宗的认可。此后两座官窑始终为宋廷承担着烧造礼器以及其他陈设器、生活用瓷的使命,直到南宋灭亡。
尽管存世量稀少,但官窑位列五大名窑的显赫地位始终无法撼动。因为正是自南宋官窑始,瓷器不再只是用于饮食的餐具、茶具或是陈设、把玩的生活用品,而一跃成为国家正式典礼所用的祭器。这些造型古典的器物最初为宫廷庙堂采用,后来向中下层社会普及,深刻影响了世俗日常生活,这种瓷器复古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依然很常见。可以说,南宋官窑的设立,让瓷器的礼器功能开始彰显,开辟了新路线,尽管这背后藏着一段山河破碎风飘絮的血泪史,但它们对社会及后世造成的深远影响,也足以让其在众多名窑里独树一帜。
作者 | 周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