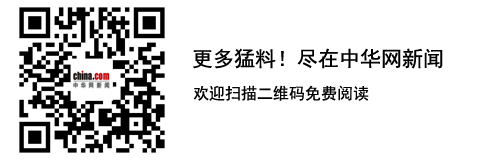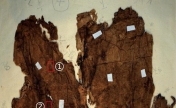王震中:“大一统”思想的由来与演进
摘 要: “大一统”思想是由“大一统”政治而产生的,“大一统”政治主要体现于“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结构,因此,我们考察“大一统”思想的由来与演进,必须从我国古代国家形态结构的演变历程着手。从秦汉到明清,“大一统”思想是建立在“郡县制”国家形态结构之上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历代王朝都把统一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即使在分裂时期,在思想意识上仍旧是统一的,割据势力往往把自身说成是正统,把统一作为奋斗目标。从秦汉上溯到春秋战国,作为社会的转型期,其“大一统”思想,既有人们对于统一的理想,更因为有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国家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这一历史渊源。从三代再往前追溯,五帝时代在中原地区建有实力强大的“族邦联盟”。这样,从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伴随着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先后产生了三种背景指向的“大一统”观念:即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与夏商西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观念;与秦汉以后郡县制机制下中央集权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这就是中国“大一统”思想的由来和演进。
关键词: 大一统; 郡县制; 复合制王朝国家; 族邦联盟
“大一统”思想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但是对于它的由来和演进,学者们并没有太多的深究。殊不知,“大一统”思想与“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结构及其认同,密不可分。因此对于“大一统”思想演变的探究,牵扯到对我国古代国家形态结构演变历程的研究。在这里,我们欲通过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结构的演变轨迹来认识“大一统”思想的演进历程。
一 “郡县制”国家结构与“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来源于“大一统”的国家社会。中国历史上真正“大一统”国家始于秦朝,这是史学界的共识。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史记·秦本纪》说:“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 [1]220其国家的形态结构与夏商西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诸侯,建立起单一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这是一种“中央—郡县”一元化的行政体制。全国境内的“多民族”被纳入郡县这样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由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可打散乃至融化族群上的差异;郡县控制了地方,郡县制有利于集权和统一。秦始皇为了巩固统一,推行“车同轨”,统一交通;“书同文”,统一文字;统一货币和度量衡。这些统一措施与郡县制一起,对此后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国家维护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承秦制,秦汉之后,尽管在地方行政管理的层级上,各个朝代互有差异,有的实行郡县(州县)两级制,有的实行省府县三级或四级制,但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依旧统称为“郡县制”。“郡县制”这样的体制机制及由此而呈现出的国家形态结构,是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与一元化的“中央—郡县”制体制相适应的是“大一统”思想,也就是说,从秦汉到明清,“大一统”思想是建立在“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结构之上的。尽管从秦汉开始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历史循环,例如从秦汉的统一到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再到隋唐的统一;从五代、宋、辽金西夏的分裂,再到元明清的统一,但是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统一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的总趋势,究其原因,我以为有三个方面:第一,就国家管理治理而言,一元化的“中央—郡县”制,既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很难逆转的。第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历代王朝都把统一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即使在分裂时期,在思想意识上仍旧是统一的,割据势力往往把自身说成是正统,把统一作为奋斗目标。第三,有一个以统一的文字为基础的包括“大一统”思想在内的具有“大中华文化”思想意识的文化传统,在根本上是维护统一的。
就一元化的“中央—郡县”制既是行之有效的又是不可逆转而论,统一时期自不待言,即使分裂时期,各个割据政权在其统辖的范围内,其统治方式也是以一元化的“中央—郡县”制为其基本特征。例如,三国鼎立,北方的魏国虽然在统治机构和职能上有所调整,曹操还提出过“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方式,但这些都是与由中央统辖的“州—郡—县”结构及其一元化统治方式相适应的。蜀国也是这样。诸葛亮在受刘备托孤辅助后主之后,除了认真实行他在《隆中对》中提出的“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进而北伐以成霸业,兴汉室的治国方针之外 [2],在蜀国的治理范围内,也是由中央一元化统辖的州郡或郡县结构。吴国在军事和经济上和曹魏一样推行屯田制度,并分为军屯和民屯,进一步开发了江南经济,在其治理范围内也是由中央统辖的州郡县结构。再比如,南北朝时期,统一北方的前秦,在地方行政上仿照魏晋,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制,由刺史或州牧掌管一州。
历史上,割据政权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只要有可能,总是要走向一统天下的轨道,总是想以正统自居,总是要以统一作为奋斗目标。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为“五胡”的那些由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们,每每运用自战国秦汉形成的“土、木、金、火、水”依次相胜传递的“五德终始”说,来主张自己统治的正统性。据《晋书·载记》,匈奴族前赵刘曜、羯族后赵石勒,皆承金为水德。前燕鲜卑族慕容儁即位,群下言承黑精之君,代金行之,慕容儁从之。又据《晋书·慕容暐载记》:郭钦奏议,以暐承石季龙为木德,暐从之。这是说,前燕鲜卑族“五德”相承具体哪一德的说法,在慕容儁与慕容暐之间有变化,但他们信奉“五德终始”说是没问题的。羌族姚苌建立后秦政权,《晋书·姚苌载记》:姚苌即位,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前秦苻坚乃氐族之人,但据《晋书·苻坚载记》,苻坚相信王彫的说法,自以为是颛顼之后,从相胜之说,乃得为木德。北魏也是这样。据《魏书·礼志》,大祖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昭有司定行次,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 [3]351-352。
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他们之所以承袭之前中原王朝所信奉的改朝易代的“五德终始”说,其目的即在于宣传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对此,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已有很好的研究 [3]12-26。此时由“五德终始”说表现出的正统论是与“大一统”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前秦苻坚在王猛辅佐下,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并出兵消灭了前燕、前凉、代,统一了北方。苻坚统一北方之后,一方面相信自己是“五德”循环之中的木德,另一方面他积极图谋攻打东晋,要一举统一中国。但是由于他统一的北方尚不稳固,前秦国内民族矛盾依旧严重,而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误认为东晋已是“垂亡之国”,不听劝阻,骄傲冒进,倾全国之力,想一举吞灭东晋。结果经淝水之战一役,大败而归,随之前秦政权陷入土崩瓦解,次年灭于后秦。我们说,苻坚统一中国的目标无可指责,也是受“大一统”思想主导的,但当时实现统一的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时机不对,再加上战役指挥上的失误,所以只能造成自己的遗憾。
在我国历史上,从秦汉到明清,“大一统”的思想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大一统”思想形成了一种传统,是正统思想,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中基因性的要素;第二,在“大一统”思想意识中,国家的统一、对国家统一的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乃三位一体的关系。
二 春秋战国时的“大一统”思想及其渊源
我们说,司马迁《史记》中的“大一统”史学观、董仲舒所阐述的“春秋大一统”思想,都是既有当时现实社会的基础,亦有历史渊源。司马迁和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现实基础,是秦汉时期所建立的一元化“中央—郡县”制国家结构,即我们一般所称作的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司马迁《史记》中“大一统”史学观的历史渊源则是先秦典籍对于五帝的记述以及夏商西周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
一般认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史料主要来自《尚书》的《尧典》《皋陶谟》以及战国末年编写成的《大戴礼记》的《帝系》和《五帝德》等。《尧典》《皋陶谟》《禹贡》是《尚书》的前三篇,以前传统史学认为《尧典》是唐虞时之作,《皋陶谟》是虞舜时之作,《禹贡》是夏禹时之作。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过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学者们的考辨,现一般赞成《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这三篇写定在春秋战国时期 1 [4]22,刘起釪进一步提出《尧典》是孔子搜集上古流传下来的材料,编辑而成,用于对孔门弟子的教学,即《尧典》的编成经孔子之手,到战国时孔门七十子后学承传之,可能有所传异增写;《皋陶谟》的内容见于春秋早期,自后继续传诵下来;《禹贡》的写作时代,刘起釪认为王国维、辛树帜主张成书于西周之说有其合理性,但又受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一文影响,认为《禹贡》蓝本出于商朝史官之手,由周初史官写定,流传到战国时又增加了一些战国史实 [5]384,509,840-842。总之,《尚书》中的《尧典》和《皋陶谟》保存了大量口耳相传的远古材料,在春秋战国时期最后写定。写定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就会反映出这一时代的一些思想观念,其中的“大一统”思想观念就是一个核心观念。例如,《尧典》和《皋陶谟》中把原本属于不同部族的尧、舜、驩兜、共工、四岳、皋陶、益、夔、禹等在“族邦联盟”中的活动和议事,安排为尧、舜朝廷里的大臣,就是以“大一统”思想为基本理念的。《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尧舜的描写就取材于《尧典》和《皋陶谟》,只是很多都改写为汉代语言。所以,我们说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渊源是春秋战国时的典籍文献,当然也与我们后面要论述的夏商西周王朝国家的形态结构有关系。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渊源来自《春秋公羊传》。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说:
《春秋》曰“王正月”……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
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
文中的“一统于天下”即“大一统”之义。如《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也。”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来源于《春秋公羊传》。《公羊传》隐公元年曰:“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写定于汉初,杨伯峻说:“《公羊传》何休《序》徐彦《疏》引戴弘《公羊序》说《公羊》‘至汉景帝时,寿(公羊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则《公羊》写于西汉有明文可据。《四库全书提要》直定《公羊传》为公羊寿所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 [6]24这样,我们看到汉景帝时的公羊寿和汉武帝时的董仲舒讲的“《春秋》大一统”,都来源于对《春秋》纪年历法使用“王正月”的阐释。
现在作为经书的《春秋》原本是鲁国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的编年史,并经孔子整理修订。《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1]1934所以,一般认为《春秋》笔法包含有孔子的思想意识。《春秋》“王正月”之王是周王,“王正月”是说《春秋》纪年使用的历法是周历,这反映了鲁国及孔子在用心地维护周王的正统地位。相传周王朝于每年末颁布明年历书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因而,何谓“王正月”?以周王颁布的历法一统于天下也。由此,我们说,现在所说的“大一统”指的是空间,而《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是“一统”于周历的,是从周历正朔这种具有“时间”指向的概念出发的。当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已有把历法正朔上的一统转化为空间上的一统,这就是该文所说的“是故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要之,《公羊传》和董仲舒“《春秋》大一统”思想,其历史渊源即在于经孔子整理修订的《春秋》纪年历法使用周历即王历的做法。
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从《尚书》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大戴礼记》的《帝系》《五帝德》等篇,以及《春秋》使用王历以强调正统和一统的做法,可以看到其“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之外,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其编纂的内容、结构和体例也透露出“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就连邹衍的大九州论中也包含着“大一统”思想要素。在诸子的著述中,也可以看到“大一统”思想观念,如《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说:“不嗜杀者能一之。” [7]71这里的“一”就是“统一”。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说这段话清楚地表现了时代的愿望。
对于战国时期“大一统”观念形成的原因,一般的解释是人民苦于战争和各国以邻为壑等灾难而迫切希望统一。我以为这只说对了一个方面,但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时期,处于由“宗子贵族社会”转向“地主官僚社会”,其中在战国时期,战国七雄等国都属于主权独立的国家,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的互动关系来说,我们很难说战国时期的“大一统”思想是从战国时独立而纷争的诸国现实直接产生的。实际上,春秋战国时的“大一统”思想渊源于夏商西周时的“一统”思想,而夏商西周时期的“一统”思想又是以这一时期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形态结构”这样的现实为基础的。
三 夏商西周复合制国家形态结构与“大一统”思想
关于夏商西周三代国家形态结构,以往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夏商西周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 8-9]。这种观点虽然方便解释战国时“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渊源,但其“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说”本身却脱离了历史的真实。夏商西周时期的诸侯邦国与后世郡县制下的行政机构或行政级别不同,不是一类:(1)夏商西周三代各个诸侯邦国的国君是世袭的,秦汉郡县行政长官却是任免的;(2)有一些夏商西周王朝的属邦是夏朝商朝周朝之前即已存在的邦国,在夏商西周时这些属邦与夏王商王周王有隶属或从属关系,可以受夏王的调遣和支配,但并非像秦汉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级辖一级的权力机构;(3)它们臣服或服属于夏商西周王朝,只是使得该邦国的主权变得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内的“国中之国”。夏王商王周王对诸侯邦国的支配是间接性的,而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则依据行政级别从中央到地方是一元化的直接支配。因此,如果把夏商西周王朝定性为与秦汉王朝差不多一样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
第二种观点则把夏商西周王朝看作是由许多方国组成的联盟 [10],这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说法忽视了夏王、商王和周王对于地方诸侯邦国的支配作用。在国土结构上,它无法解释《诗经•小雅•北山》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法解释《左传》昭公九年周天子的大臣詹桓伯所说西部岐山和山西一带的“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东部齐鲁之地的“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南方的“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北部的“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等事实。它忽视了诸侯邦国在政治上不具有独立主权;在经济上要向朝廷贡纳,经济资源尤其是战略资源要输送到中央王国;在军事上,地方邦国的军队要随王出征或接受王的命令出征。也就是说,从属于王朝的诸侯邦国,以王为“天下共主”,受王的调遣和支配,虽然这些诸侯邦国内部并没有与王建立层层隶属关系,王对他们只具有间接支配关系,但包括各诸侯邦国在内的整个王朝是一种“多元一体”。
针对上述两种观点的局限性,我提出了“夏商西周三代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所谓“复合制国家结构”,就像复合函数的函数套函数那样,处于“外服”的各个诸侯邦国是王朝内的“国中之国”;处于“内服”的王邦即王国,属于王朝内的“国上之国”,是王权的依靠和基础,而“内外服”又是一体的 [ 11-12][13]436-440,471-485。
具体说来,商周王朝的复合制即“内外服”制,可由《尚书》和金文得到说明。在周初的诸诰中,关于商的内服、外服之制,《尚书·酒诰》一篇说得最为详备:
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5]1403
《酒诰》这段材料记载了商王朝结构分内、外两服,其内服为:百僚、庶尹、亚服、宗工,还有百姓里君,属于在朝为官的百官系统;其外服为:侯、甸、男、卫、邦伯,属于王邦之外的诸侯邦国系统。《酒诰》的记载恰可以与《大盂鼎》“惟殷边侯田(甸)粤殷正百辟”铭文对读。铭文中的“殷边侯田”,是说殷商的边鄙之地侯和甸这样的诸侯;“殷正百辟”中的“正”是官职的意思,“辟”是君的意思,“殷正百辟”就是在朝为官的百官的意思。“粤”是连接词,是与的意思。这样,《酒诰》篇所说“侯、甸、男、卫、邦伯”之类的“外服”,就与《大盂鼎》“殷边侯田(甸)”对应了起来;《酒诰》篇所说“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百姓里君”之类的“内服”,就与《大盂鼎》“殷正百辟” 对应了起来,由此可证《酒诰》文献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也是可信的。
西周的情况也是这样,实行的也是“内、外服”制。西周的内服即周王直接掌控的周邦(王国),西周的外服即周王分封的、不具有独立主权的诸侯邦国,二者在王权的统辖下构成多元一统(多元一体)的西周王朝国家。
对于西周的复合制国家结构,也见于《尚书》和西周金文材料。《尚书·康诰》: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 [5]1292
《尚书·召诰》: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5]1433-1434
《康诰》中的“侯、甸、男、邦、采、卫”,属于“外服”的诸侯系统;“百工、播民”,属于“内服”系统,“百工”即百官,“播民”即迁徙到东都洛邑的殷民。《召诰》中的“庶殷”即迁徙到洛邑的殷遗民,地处王畿“内服”之地;“侯、甸、男、邦伯”即“外服”诸侯系统。
《康诰》《召诰》所说的“内、外服”制,也可以和西周青铜器铭文对应起来。《夨令方彝》:“舍三事令,眔卿事寮,眔里君,眔百工,眔诸侯:侯、甸、男,舍四方令。”铭文中的“卿事寮、里君、百工”,属于“内服”的百官系统;与此相对应的“四方”诸侯——侯、甸、男,属于诸侯邦国系统。西周所谓分封制,分邦建国的就是“外服”诸侯系统,它与在朝为官的“内服”系统合起来,共同构成“复合制的王朝国家结构”。
西周青铜器铭文《大盂鼎》和《夨令方彝》所记载的“内、外服”制,与西周文献《尚书》中《酒诰》《康诰》《召诰》所记载的商周“内、外服”制完全对应,这正是王国维所说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与地上传世的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显例。
商周王朝复合制国家结构体现在政治区域的划分上,固然由内服与外服即由王邦与诸侯邦国所构成,但这种划分并非使二者截然分离,连接二者一个很好的纽带就是诸侯邦国的一些人作为朝臣,住在王都,参与王室的一些事务。以商代为例,在甲骨卜辞中有一个担任“小臣”官职的“小臣醜” (《合集》36419),这是一位在朝廷为官者。这位在朝为官的“小臣醜”,来自山东青州苏埠屯1号大墓“亚醜” [ 14-15]诸侯国。类似的例子在甲骨文和殷墟出土的墓葬中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殷墟花园庄54号墓是一座在朝为官的显赫贵族墓,墓内出土的青铜礼器上,大多有铭文“亚长”二字 [16]。而长族邦君在甲骨文中被称为“长伯” (《合集》6987正)或“长子”(《合集》27641),卜辞中长族将领“长友角”“长友唐”也甚为有名(《合集》6057正、6063反等)。将殷墟花园庄54号墓与甲骨文有关长族邦君和将领的记录相联系,可以得出殷墟花园庄54号墓墓主人当为长族派遣到殷都在朝为武官的大贵族。此外,诸如在今安阳梅园庄村墓地族徽铭文“光”的家族,就是甲骨卜辞中被称为“光”(《合集》94正,《合集》182等)以及被称为“侯光”(《合集》20057)的诸侯国派遣到殷都在朝廷为官者
诸如此类,还有许多 [13]477-485。商代这些“外服”即“四土”之地的诸侯国(属邦)之人,之所以能在“内服”之地即王国中任职,就在于商王朝是由内、外服构成的复合制国家结构的缘故。
由商周上溯到夏代,从先秦文献和《史记·夏本纪》中可以看到:在夏王朝中,既有作为王邦的夏后氏;也有与夏后氏同姓的国族,如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还有以服属地位出现的韦、顾、昆吾、有虞氏、商侯、薛国之类的诸侯邦国,所以,夏朝国家结构是由多种“共同体”构成的多层次的以夏王为“天下共主”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
在夏王朝中,夏后氏与诸侯邦国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如《左传》宣公三年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 [6]669《孟子·滕文公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 [7]334就是说这些诸侯邦国是要向王邦纳贡的。《墨子·耕柱》说:“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 [17]蜚廉为秦之先祖,夏启使秦的蜚廉为他采矿冶金,这也是一种纳贡的方式。
《左传》上还说薛国之君奚仲担任夏的车正之官,专门造车,为夏王提供车辆。商侯冥担任夏的水官,因治水而殉职。《国语·周语上》说周族先祖曾经“服事虞夏”。这些诸侯邦国的邦君或贵族,在王朝中央任职,既是对王朝国家事务的参与,亦是对中央王国这个天下共主的认可;而作为邦国又分处各地,则发挥着蕃屏王邦,守土守疆的责任。
这样,我们说夏商西周三代都属于复合制王朝国家,复合制呈现出的是“多元一体”:“多元”是说它是由许多不同姓族的人们组成,包含有许多诸侯邦国;“一体”是说整个王朝国家具有一体性。这样,生活在复合制王朝中的周人,自认为自己的王朝是“统一”的,这就是前引《诗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云云的社会基础。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曾有“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的感叹,也是鉴于他所向往的西周是“统一”的。与秦汉以来郡县制机制下一元化的“大一统”思想观念相对而言,从“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产生出来的“大一统”观念,则属于相对早期的“大一统”观念。这样的一统观念在三代王朝代代相传,构成了一种正统观念。到了战国时期,当人们苦于列国纷争时,盼望统一,既是现实愿望,也有历史渊源。
四 五帝时代的“族邦联盟”与“大一统”思想
从三代再往前追溯,《史记•五帝本纪》所说的五帝时代以及《尧典》《禹贡》所说的颛顼尧舜禹时期,其政治实体的形态结构又是什么样子呢?以往的观点大多认为,包括尧舜在内的五帝时代是“部落联盟”。我近十多年的研究认为,当时固然是一种联盟,但它不是“部落联盟”,而是“族邦联盟”,或可称“邦国联盟”。
五帝时代中原地区的“族邦联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第二阶段是尧舜禹时期。黄帝时期的“族邦联盟”形成于黄帝战胜炎帝和蚩尤之后的联合。
根据《国语•晋语四》,黄帝族与炎帝族原本是“兄弟”关系。如《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18]这说明炎帝与黄帝二族都出自上古时代陕甘地区的一个大的部族或“部落联盟”。但是,黄帝族与炎帝族在由西向东迁徙发展的过程中,又因各自的扩张而发生冲突。《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1]3
炎黄阪泉大战之后,炎黄联合又与蚩尤发生涿鹿大战。《逸周书•尝麦解》记载:
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19]
引文中的“赤帝”即炎帝,这条记载表达的意思大体上是:在上古之世,上帝命炎帝分设二位卿官,让蚩尤居住于少昊之地管理天下百姓,但蚩尤为了向外扩展,驱逐炎帝,占领炎帝的土地,致使“九隅无遗”。炎帝十分害怕,只好求助于黄帝,黄帝在“中冀”这个地方杀了蚩尤,用少昊清(名“质”)代替蚩尤来统率东方,稳定了天下秩序。
蚩尤原来是“于宇少昊(居住在少昊之地),以临四方”。蚩尤被杀之后,黄帝让少昊清(少昊质)代替蚩尤,“以正五帝之官”。关于蚩尤的族属,徐旭生主张蚩尤属于东夷族 [4]50-53;汉代的高诱、马融等人都说蚩尤是九黎的君名,而九黎一般被认为属于三苗集团。这里暂不讨论蚩尤的族属,仅就黄帝让少昊清代替蚩尤统领东方诸部而论,其背景应该是此时的黄帝族与东夷族结成了联盟,黄帝为盟主,以少昊清为首领的东夷族是盟友。可作为这一情况旁证的是《韩非子•十过》的一段话:“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 [20]69这段话是用神话的方式表达了一些史实。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风伯、雨师都是在逐鹿大战中蚩尤请来“纵大风雨”、用以对付黄帝的风神和雨神,现在却成为“黄帝合鬼神于泰山”时与蚩尤一同为黄帝的到来而“进扫”“洒道”者。就连蚩尤以及风伯雨师都归于黄帝麾下了,那么替代蚩尤的少昊诸部与黄帝族结为友好联盟,更属情理之中。在古史传说中,人名、族名和神名每每可以相同一 [21]76,《韩非子•十过》这段属于神话与历史相交融的话中,既有人名与族名(如蚩尤与蚩尤族)相同一的情形,也有人与神(如风伯雨师与风神雨神以及死后的蚩尤等)相同一的情形。所以,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之后,不但黄帝族与炎帝族结为联盟,黄帝族与东夷族也结为联盟。
关于尧舜禹时期的“族邦联盟”,一般由《尚书·尧典》等文献所讲的尧舜禹禅让加以说明。例如,《尧典》:
尧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型)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5]86
文中的“汝能庸巽朕位”,《史记·五帝本纪》写作“汝能庸命,践朕位”,“庸命”即用命,意为遵用上命,很好地贯彻执行命令。开头这两句,帝尧说:“唉!四岳,我在位七十年了,只有你能完成我交给你的使命,你来接替我的帝位吧。”四岳回答说:“否德忝帝位。”意思是“我的德行鄙陋,有辱帝位”。帝尧曰“明明扬侧陋”,《五帝本纪》写作“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是让“考察推举贵戚中的贤德之人,或隐匿在民间尚无名气的贤才”。“师锡帝曰”,《五帝本纪》写作“众皆言于尧曰”:有一个身处底层的单身汉,名叫虞舜,是这样的贤才。帝尧说:“是啊!我也听说过,到底他的情况如何呢?”四岳说:“是一个瞎老头的儿子,父亲愚顽,继母凶狠,同父异母弟弟象却傲慢逞强。但舜以自己的孝行感动全家和睦相处,家庭生活蒸蒸日上,家人们也都不至于再有奸邪行为。”帝尧说:“那我就试试他吧!”“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五帝本纪》写作“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二女下嫁到舜的居地妫汭,即今山西永济妫水弯曲的地方,做了虞舜的妻子。帝尧勉励虞舜说:“恭敬地处理政务,好好干吧!” [5]353《尚书·尧典》这段话生动地描写了唐尧把“族邦联盟”盟主之位禅让于虞舜的过程。
也有先秦文献说尧舜禹不是禅让而是“逼宫”,如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韩非子·说疑》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20]417我认为这两种说法反映出当时的“族邦联盟”盟主职位在联盟内转移和交接有两种情形:“禅让说”说的是盟主之位在联盟内的和平转移和交接;“逼宫说”说的是尧舜禹相互之间有争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地区各个邦国之间势力消长的关系。但不论何种,尧舜禹时期在中原地区存在一个强大的“族邦联盟”是不容否认的。
当时,尧舜禹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本邦国的国君(即邦君),又是联盟的盟主。尧舜禹所禅让的或所争夺的是联盟盟主之位,并非本国国君之权位。尧舜禹时期也被称为是“万邦”时代,小国寡民的邦国林立。例如,《尚书·尧典》说尧时“协和万邦”。《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所谓“万邦”“万国”之“万”,只是极言其多而已。在这些“万邦”(“万国”)中,诸如唐尧之邦、虞舜之邦、共工氏之邦等,属于早期国家性质;也有一些尚处于部落,但事物性质总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规定的,当时已进入早期国家的各邦,代表了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政治实体,所以,当时在中原地区结成的联盟应该称为“族邦联盟”,而不能像以往那样称为“部落联盟”。“部落联盟”属于原始社会的范畴,“族邦联盟”则不限于原始社会,文明社会(国家社会)也可以使用。所以,我不赞成把《尧典》《皋陶谟》中的联盟说成是“部落联盟”,而主张是“族邦联盟”。
“族邦联盟”既不是一个王朝,也不同于后世的国家。但是,“族邦联盟”在走向“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过程中也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联盟一体”的思想观念,而春秋战国和秦汉时的人们由于不具有近代人类学所谓的“部落联盟”或“族邦联盟”之类社会科学的概念,因而只能比照夏商西周三代和秦汉时国家形态的样子来描述和表达五帝时代的社会,把尧舜禹“族邦联盟”描绘成了尧、舜朝廷,只是有时用“禅让”与“家天下”对五帝时代与三代略作区别而已。其结果是把“联盟一体”的思想观念拟化为另一层次的“大一统”观念,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说的轩辕黄帝在征战了炎帝和蚩尤之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合符釜山”的情景;这也是《五帝本纪》和《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所描述的五帝时代“天下”一统的缘由。
五 结 语
总括上述,“大一统”思想是由“大一统”政治而产生的,“大一统”政治主要体现于“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结构,因此,我们考察“大一统”思想的由来与演进,必须从我国古代国家形态结构的演变历程着手。从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伴随着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先后产生了三种背景指向的“大一统”观念:即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与夏商西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观念;与秦汉以后郡县制机制下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从思想观念的视角而言,这三种背景指向、三个层次的“大一统”思想观念,是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标识,也是中华文明连续而又有阶段特征的体现;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而言,与“大一统”思想背景相联系的是:从五帝时代“单一制的邦国”及其“族邦联盟”,发展为夏商西周三代“复合制王朝国家”,再发展为秦汉以来一元化的“中央—郡县”制的帝制王朝国家,呈现出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演进:即中国国家形态结构的演进与“大一统”政治思想演进的互动发展关系。
脚注
1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说:“(古史辨派)他们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在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时候(初写在春秋,写定在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