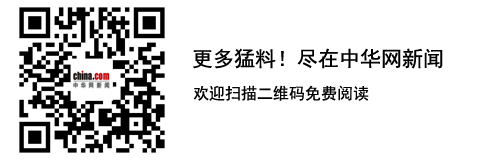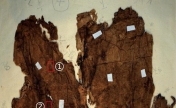在日前出版的《致用与娱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绘画》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教授高居翰(James Cahill)将注意力转向中国传统画论中被忽视的“世俗画”(Vernacular Painting)传统。
“江南百景图七狸餐馆在哪里?想买到便宜的浊酒”,这是《江南百景图》玩家社区近日以来讨论的话题之一。这款古风手游自上线日起就因水墨画风下的市井风貌而受到关注。百年前民众的俗世生活直到今天依然引人遐思,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绘画偏重文人山水,以世俗百态为题材的画作一直未能进入所谓的“主流”绘画。
在《致用与娱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绘画》中,高居翰通过对120余幅盛清世俗绘画的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画中不同于文人山水画的别样图景。经由一幅幅画卷,我们得以窥见帝王威仪背后的私人生活图景,与画师一道在不同版次的画作对比中揣摩当年圣心,也能走进江南市井街头,一睹两百多年前百姓的起居日常。在技巧方面,当时的画师选择性地对西方透视法有所吸收,在东西融合中服务于一种更具可读性的中式表达。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为何这些技艺高超的画作却长期被排斥于传统“主流”绘画之外呢?
撰文|申璐
提起世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令人印象深刻。但回溯这幅画作前后,似乎鲜少有同类作品为世人所熟知。
据高居翰在《致用与娱情》一书中介绍,实际世俗绘画一类作品在中国绘画发展的最早阶段就已出现,宋代偶有名作问世,但大规模且多样化的创作集中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明代末期,中国社会逐渐从以农为本的社会中发展出早期城市化与商业化的雏形。生活富足的商人群体也渴望体验昔日为文人士绅、朝廷官吏所独享的文雅生活,这构成推动城市画坊画师快速兴起的市场推力。加之雕版印刷技艺日渐成熟,为城市印刷文化的规模化提供技术支撑。这些都使得明末之后的盛清(主要指“康雍乾盛世”)成为应雇主要求而作的世俗画发育的沃土。
《致用与娱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绘画》,【美】高居翰著杨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1月
给予与流露:
清代世俗画中的形象推拉
清代世俗画师大致可分为供职于宫中的宫廷画匠和处江湖之远的城市画人。虽然都是应雇主要求绘制功能性的作品,但皇家“雇主”对画作的完整性以及是否适宜正式展示都有着更为严苛的要求。
宫廷画院的画家多来自南方城市,他们往往由朝廷官员的乡人引荐,后经皇帝钦准方能入宫,有时皇帝在每年南巡途中,也会从呈献作品的当地画师中挑选中意的人。这些画人在入宫前往往已经具备精湛的绘画技巧,能够为特定的场合或用途定制画作,有些甚至多领域兼顾,不但擅长人物肖像还精通亭台楼阁的描摹。此外,由于宫中常常有大型庆典的记录任务,或是王公大臣、后宫嫔妃的肖像速写,因而写实派的画人越是隐去个人绘画特色,越是能够融入群体合画中。毕竟在这样的画作中,皇帝关心的并非是各家画风,而是在群臣、后妃簇拥的场景中,自己是否足够醒目。
图1佚名(可能出自张震或张为邦,或其他画家)雍正行乐图轴绢本设色206厘米×101.6厘米故宫博物院
为做说明,高居翰在书中援引了多幅画作。其中,这幅高约2米的《雍正行乐图》【图1】描绘的就是雍正在圆明园中的私人生活图景。画中雍正帝位于前景,独坐于水榭之中,与嫔妃相隔甚至目光都并无交集,以此凸显帝王威仪。随着视线向画面纵深处延展,嫔妃和侍女恭候在不远处,回廊处另有三位妃子巧笑盈盈,谈笑间目光似停留于两小儿嬉戏。那么,如何在不失帝王威仪的同时表达“行乐”意蕴?宫廷画作的细微处传递着微妙信息。画中左下角的白猫正与一对白鼠对峙,尽数落在半藏于树干后的花猫眼中;中景处,一条黑白犬几欲起跳、越过栅栏去和另一只白犬嬉闹;不远处的一双仙鹤目光交合。成双成对的动物寓意殷勤的男性在追求婀娜女性,也是皇帝与嫔妃关系的隐晦注脚。
此外,高居翰还关注到,画中嫔妃并未着满族服饰,皆身穿汉服,她们很可能是汉人妃子的写照。但这似乎又于当时的礼法不和,清廷自立国始就对女子着汉服有所限制。那么这幅画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吗?那些宫墙禁令是否在帝王私下生活里都有所松弛,抑或这实则是满族皇帝在保有公开形象中的文化纯粹性的同时,尝试调和与汉人儒家间紧张关系的一种手段。
图2可能与图3出自同一组人物画家乾隆行乐图轴绢本设色227.2厘米×160.2厘米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