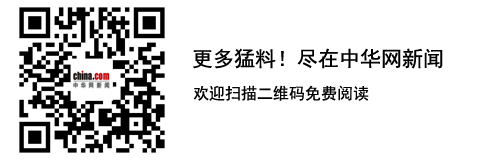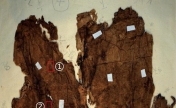在此,柏拉图的洞穴问题再度浮现。
在柏拉图的思考里,洞穴中的“囚徒”处于黑暗和迷信的状态,火在他们身后燃烧,而他们只能够看见投射到墙壁上的画像。借用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说法,这其实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视野,可以叫作自然洞穴。而在现代知识社会,在这个洞穴下方更深处,还出现了一个由人挖掘的洞穴。所谓“在此之后,因此之故”,一个人从进入学科专业训练起,就可能从自然洞穴掉到人为洞穴,唯有取掉身上的枷锁才可能往上爬升,重返自然洞穴,恢复使用生活语言和整体性思维。
我们若往人造洞穴探一探头就会发现,在形式上,社会科学研究由问题、文献、研究假设、测量、分析和结论等格式组成。任何一种研究或发现都以此为标准按部就班,在适当的地方提出适当创新的看法。当然,这保证了学术共同体高效交流的可能性,不必读完全文,只要找到相应板块就可“按需阅读”。国内学者彭玉生的《“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将此形容为“洋八股”,并肯定了它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的意义——使研究者能戴着枷锁“跳舞”。
就此而言,甚至还可以说,其实人造洞穴也不是最深的,因为在它下面还有一堆像蜜蜂窝似的“人造洞穴群”。每个研究者居于一种人造洞穴,相邻的洞穴尚可往来,再远一些就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他们只有飞出去,离开“自说自话”的洞穴,才能来到统一的、有对话基础的人造洞穴。而学术规范则是推动研究者去往人造洞穴的条件。这也是在世纪之交邓正来等人致力于汉语学术规范化的重要依据,在此前,即便是《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这样的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也没多少学术规范讲究。
不过悖论的是,当研究者终于来到人造洞穴后,学术规范却成为社会科学下一步的藩篱,阻碍人继续往上升。当然满足于此的人是可以积攒学术界内的声誉。唯有“离经叛道者”拒绝循规蹈矩,踏上冒险之路,试图离开人造洞穴上升至自然洞穴,虽然那也只是墙壁上的画像罢了。这也是米尔斯的主张,他批评抽象的宏大理论和数据实证主义,呼吁社会科学研究面向我们共同所处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自然洞穴。
如果研究者终于找到某种形式(“离经叛道”是其中一种)攀爬至自然洞穴,回到我们共同的生活世界,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什么?
碎片化的“结构”
第一个问题是“结构”。

20世纪早期德国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1927)剧照。
“结构”的主要内容是差异分布。我们可以想象此刻站在城市的某座高层大厦,走向窗户,一眼望去,在外面那个可见的世界,有的楼正在改建,有的楼还未封顶,有的楼高,有的楼矮,有高级住宅、写字楼,也有拥挤的平房,而在建筑之间还横七竖八排列着街道。它们组成的就是结构。在社会意义上,如果某个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在收入、性别、教育等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也就形成了结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大多数时候原本就在谈论结构问题。每一项社会调查研究都是收集数据描述一个或多个人群、一个或多个阶层、一个或多个地域,而它们内部的差异,是之所以有必要做调查的前提,哪怕最终差异不显著,至少在提出假设阶段也可能会认为存在差异并对它进行检验、解释。
米尔斯的想法是希望人们都能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把握世事进展,理解自身遭遇”,能发现和解释“周边世界”,把个体处境想象为某个公共问题。结构性思考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也就自然形成了。

《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美]小威廉·休厄尔著,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
问题在于,就像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在《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见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2021年7月)中提醒的,人们看见了结构的力量,可是把它视为是决定性的、单数的,而结构是复数的。这启示着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同一个现象其背后有多个结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结构起了作用,当研究者用某种结构去分析问题时,是否会因为价值立场而选择性忽视其他结构。这是米尔斯并未怎么反思的问题。他关注的问题是“对手”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等人的局限,后者主张社会科学必须研究具体的、经验的问题,而不是企图“一夜之间拯救世界”,发现整个社会结构。
米尔斯认为“现代”的结构和动力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命题,“社会科学家希望理解当下这个时代的性质,勾勒其结构,捕捉其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力量”。他举例说,政治学家研究现代国家、经济学家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学家的问题中也有许多是从“现时代的特征”的角度来提的。当然,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产生就源自现代性,因此绝大多数社会学教材的前言或第一章都以现代社会和社会学的关系作为开头,从19世纪讲起。
然而,这并不等同于“现代”“结构”等问题得到与此匹配的思考。“现代”涉及人、权利和权力等根本性问题,却被默认为是过去的、旧时的,是不如“后现代”新潮的,或者只是某个具体问题的注脚而已。米尔斯质疑过度碎片化的社会调查研究,也质疑它们能自发汇聚起来实现整合,他认为研究者需要的是思考所处社会的整体性现实以及其后的根本性结构。
也因此,沈原等国内社会学家提出,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需要直面和回应时代关键问题的研究能力,提前接受“后现代”碎片化范式就失去了这样的能力(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阶级与社会》,2007年1月),陈映芳将此称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异时代”(见《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4期的《范式与经验之间》)。米尔斯站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的也是当时的碎片化调查研究,并怀念19世纪末的赫伯特·斯宾塞,后者在《个体与国家》(见商务印书馆中文版,2021年12月)等书中对所处时代的人和社会进行了整体性思考。
缺失的历史感
再来看历史、“历史感”。历史和结构是人类思考的两种基础概念,结构体现的是横向的差异分布,历史表现的则是纵向的差异分布,也就是时间的次序。米尔斯认为历史感、时间性也是想象力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家如果不运用历史,不对心理的东西有历史的感受,就不能充分说清某些问题”。确实,社会中的人都是历史性的产物。个体的语言、观念、制度和文化都来自于既定的社会,而整个社会的秩序都是在历史中形成。
甚至还可以说,社会科学通过社会调查、田野研究收集的材料,也只不过是在某种时间刻度如“年”“月”的测量之下才是“现在的”,而实际上在问卷、访谈或观察完成的那一瞬间,手中的经验材料已变为“史料”。当然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源于变化,如果没有意识到研究对象出现变化,经验材料似乎仍然是“现在的”“最新的”,只有当意识到变化才会发现已经属于过去。

米尔斯和他的书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