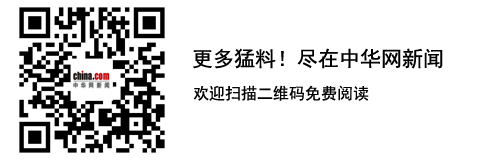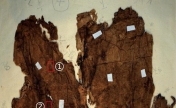广东六榕寺的花塔。
乐嘉藻也是伯施曼著作的获益者。这位在中年就立志研究中国建筑的学者在晚年曾对自己拥有的研究条件不无感慨地说:“其初预定之计划,本以实物观察为主要,而室家累人,游历之费无出。故除旧京之外,各省调查,直付梦想。”所幸的是,当时的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为他提供了方便。所以他又说:“幸生当斯世,照相与印刷业之发达,风景片中不少建筑物,故虽不出都市,而尚可求之纸面。”将乐嘉藻的《中国建筑史》与伯施曼的两部著作比对,可以看出伯施曼的著作就是乐嘉藻这些纸面材料的一部分。例如乐嘉藻著作的第13章(“城市”)的“辽金元明四朝北京沿革图”中的元、明部分就当参照了《中国建筑》的“北京的平面图”一图。此外,他还根据伯施曼著作的图片描绘了一些插图。

左图为浙江普陀山的太子塔,右图为北京玉泉山的五彩琉璃塔。
茂飞的设计以及乐嘉藻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或参照或描摹了伯施曼著作中的图片,这一发现促使我们在更大的范围里考察后者的影响。事实上伯施曼的著作不仅嘉惠了茂飞和乐嘉藻二人,也是其他一些中国建筑师和建筑史家参考甚至批判的对象。
郭伟杰指出南京阵亡将士公墓的六柱五楼大牌楼是由当时在茂飞事务所工作的董大酉经手设计的。这一事实说明了董大酉受到了伯施曼著作的影响。这一影响至少还可见于董大酉在1931年设计的大上海体育馆。对比它与《中国建筑》中“北京碧云寺汉白玉塔”两座建筑须弥座束腰部位的玛瑙柱子和椀花结带图案的造型,我们就能看出二者的关联,尽管董大酉制作的须弥座的上枭和下枭都有所简化。
此外,营造学社社员、建筑师卢树森在1935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园的藏经楼也得益于《中国建筑》。这座颇为纯粹的清代官式风格建筑看起来在书中并没有对应的实物,不过它与伯施曼著作中的“苏州玄妙观弥罗阁”均在歇山形屋顶上另加一个略小的悬山顶,这一共同特征正好体现了二者的关联。如何将中国建筑的屋顶改造为有用的空间是现代中国风格建筑设计的一个挑战。
曾有建筑师试图按照西方的办法在中式屋顶上开辟老虎窗以便通风和采光,但结果却造成了屋顶中式风格的弱化。弥罗阁的这一手法——将歇山顶中央升高,附加悬山顶,利用两个屋顶之间的间隔开窗,为藏经楼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本。卢树森作品中的藏经楼与伯施曼著作中的弥罗阁的不同体现了一种规范化的努力,即建筑师并没有照搬原来的建筑风格,而是采用了清代官式建筑的做法,设立了平座栏杆和八角形天井(室内)。这些又都是营造学社通过研究《清式营造则例》、《营造法式》(宋代),以及调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所获得的古代官式建筑的语言。同样的屋顶做法在杨廷宝于1947年设计的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建筑上也可以看到。
1925年南京中山陵和1926年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正值伯施曼著作出版之时。两处主体建筑在整体造型和细部处理上并没有明显地效仿任何伯施曼著作提供的实例。建筑师吕彦直曾作为茂飞的绘图员,在1919年参与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中国风格校园建筑的设计,所以他对中国传统建筑的了解应当另有来源。不过从两处建筑群的个别小品和一些细部依然可以看出他曾参考了伯施曼的著作。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中山陵祭堂前广场两端的华表的柱头、柱身甚至须弥座的造型都与《中国建筑与风景》与《中国建筑》中的华表如出一辙。

南京中山陵园的藏经楼。卢树森摄于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