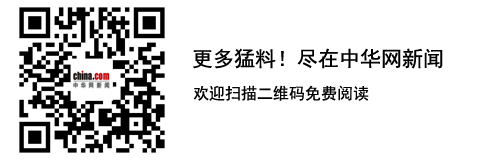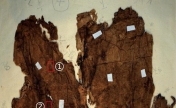意外的发现与寻宝热潮
1929年的春天,四川还处在军阀割据的状态,时常发生不间断的混战。家住在广汉中兴乡真武村的农民燕道诚,没空理会这些大事,安心本分地在自家边的水沟灌田。
他发现水流比较小,于是就找来工具,和儿子一起把水车提开,用锄头深挖水沟底部。“砰”的一声沉闷声响,让挖土过程中的燕家父子吃了一惊。刨开土看,地下有个白玉色的石环。费力掀开石环之后,发现其下另藏玄机,被遮掩的土坑之中堆满了精美的玉器和石器。
燕道诚虽是农民出身,却不是大字不识的庄稼汉。燕道诚的第四代孙燕开正公开讲述过,自己的祖上燕道诚小时候读过不少书,只因家庭矛盾,人到中年被迫搬家到了成都。那时他在县衙里做过事,当地人都称他为“燕师爷”。燕师爷看到这些宝物,一眼就认出来这些都是价值不菲的古董文物,当下不敢声张,立即把土掩埋回去。直到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才把这坑里的文物取回家。
之后的一两年里,燕道诚父子又在发现地附近陆续地做了一些挖掘工作,但收获不多。谨慎的燕道诚选择观望,没有立即把这些意外所得拿到珠宝市场上贩卖。谁料没过多久,燕道诚就得了一场大病,燕家以为可能是挖坑挖得太深,触犯到了“风水宝地”。

燕道诚全家福。
“风水”之说是当地流传下来的说法。燕道诚住在三星堆村的马牧河北岸附近,当地有一处弧形台地,呈月牙形状,被称为“月亮湾”,而河对岸又有三个圆形的黄土堆,远望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星星,和“月亮湾”遥相呼应。因此,“三星伴月”的说法也就流传开了,后来被《汉州志》收录为“汉州八景”之一,也是三星堆遗址得名的由来。
诚惶诚恐的燕道诚抱着“蚀财免灾”的心理,将挖到的大量玉石器分送和转卖给亲朋邻里。燕家偶然发现的玉器数量究竟有多少,各方说法并不相同,从“若干件”、“大批”、“三四百件之多”都有描述。后来考古工作者搜集资料后发现,这些文物中包括了玉璧、玉琮、玉圈、玉圭、石璧、石珠等各种类型的玉石器。其中又以石璧数量最多,最有特色,尺寸较大的石璧的直径达到了80厘米。
在之后三四年间,这些燕道诚挖掘后四散的文物很快流落到了二手市场上,吸引了古董商的注意。当时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从燕道诚处购得4件玉器,激动不已,又专门写了一篇《古玉考》文章发在成都一所学校的校刊上,宣称这些宝物“价值连城”,带动掀起了一股民间的寻宝热潮,而燕家挖沟发现“广汉玉”的奇闻也在转述和炒作中不胫而走。
三星堆考古发掘第一人
在关注“广汉玉”的大批人群中,也包括了一位正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Archdeacon Donnithorne)。董笃宜不是考古学者,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批流动在市场上的“广汉玉”不只是昂贵的珍玩奇宝,还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他联系自己密友,在当地驻军的陶宗伯旅长,帮助尽快找回失散文物,又借来几件玉器,邀请华西协和大学的地质学家戴谦和(Daniel Dye)鉴定。
一行人来到广汉做了初次考察,让燕道诚一家首次意识到了这些玉石器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燕家将5件玉石器赠予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即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后又赠予了挖掘物中最大的一枚石璧。经过如此一番波折,这批文物终于遇到了一位在三星堆遗址发掘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葛维汉(David Graham)。
葛维汉是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第一人。然而和董笃宜一样,作为一个美国人,葛维汉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传教,帮助当地的穷人和病人。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葛维汉和妻子在前往上海的轮船上,得知了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的巨变。从此,他们开启了前后长达三十余年的中国生活。1931年,葛维汉回到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两年之后回到成都,正式出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

葛维汉在考古发掘现场。
1934年3月,葛维汉组建了一支考古发掘队,抱着巨大的决心前往广汉。据葛维汉在《汉州(广汉)发掘简报》上的记载,等到他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当地已经抢先一步组织人手开始挖掘了。葛维汉立即向县长罗玉苍说明了非科学发掘对历史文物的严重危害,以及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罗玉苍是开明之人,不仅为葛维汉发掘队申请到了省政府教育厅的同意,还派了一支地方队伍保护他们。
适值战乱年代,广汉当地治安混乱,贼匪猖獗,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仅仅进行了十天就结束了。但考古发掘成果丰硕,出土了600多件文物和残片。作为四川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对三星堆遗址和中国西南地区文明的发源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基于这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地质学家戴谦和写了《四川古代玉器》一文,对这些出土玉石器的年代和性质做了初步的研究。更有研究价值的是葛维汉写下的《汉州(广汉)发掘简报》。他参考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对河南仰韶村以及李济在安阳殷墟主持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报告,把自己的研究整理后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上,这份报告至今仍然是考古学家研究三星堆遗址的重要参考文献。
葛维汉在报告中介绍出土文物的各种形态,并提出了“广汉文化”的观点,把遗址的年代限定在了金石并用年代到周代初期。此外,葛维汉让助手林名均给当时身在日本的郭沫若致信,寄去广汉发掘的照片和器物图形。郭沫若在回信中初步认同了葛维汉对年代的判断,并提出自己对古蜀文化的概括性看法。他认为出土文物中的玉璧、玉圭等,均和华北、中原地区的出土文物相似,这说明古代西蜀与中原有过文化接触。这封知名的书信也成为了中国考古史的重要见证。
从现在的考古研究来看,葛维汉报告中的一些观点也会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比如,葛维汉认为这些出土文物属于陪葬品,“广汉遗址”应该是一个“墓坑”。1946年郑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中单列“广汉文化”一章,介绍了葛维汉等人的考古发掘成果,其中就对“墓葬说”的观点提出了商榷。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争鸣,冥冥之中为后来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代考古学人的漫长等待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经历过长时间的中断和停滞。这样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三星堆遗址的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葛维汉的考古发掘。随着当时相关法规的出台,外国人不被许可在中国做考古发掘,抗战的爆发更是让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成为了奢望。因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三星堆的下一次考古挖掘直接来到了1986年“祭祀坑”的发现。
这样碎片化地拼接记忆,常常会遗漏很多值得记住的历史细节。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坚参与了今年三星堆遗址的三号坑发掘工作,他也被认为是第一位从今年三星堆考古现场走出来的考古学家。徐坚在一场讨论三星堆遗址的活动上指出,从1929年开始,三星堆遗址的叙事一直存在着两条平行的线索。一条是公众记忆里的三星堆遗址印象:燕道诚的初次发现、1986年“一醒惊天下”的祭祀坑发现,以及今年公布的三号坑到八号坑考古挖掘的新成果。这三次强有力的脉冲吸引了全世界持续的关注和热议,却忽略了在其之下,其实还有一条“稳定的、由数代考古学者推动、循序渐进、静水深流的学术之路”。
如果依照徐坚提供的视角,可以发现历经大半个世纪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囊括了好几代默默投身其中、却没来得及等来丰收成果的考古学家们。
上世纪50年代,因修建宝成铁路,时任西南博物院院长的冯汉骥设立工作队,沿着拟建的铁路沿线调查文物古迹,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考察月亮湾。初次考察没有太多的收获。其后,工作队中的王家佑和江甸潮从1955年到1958年又多次前往月亮湾考察,他们最终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广汉遗址”(三星堆遗址)与月亮湾遗址的文化层完全一致。他们初步判断,这两处遗址的年代相当于殷商时期,并向考古学界发出了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广汉文化”的呼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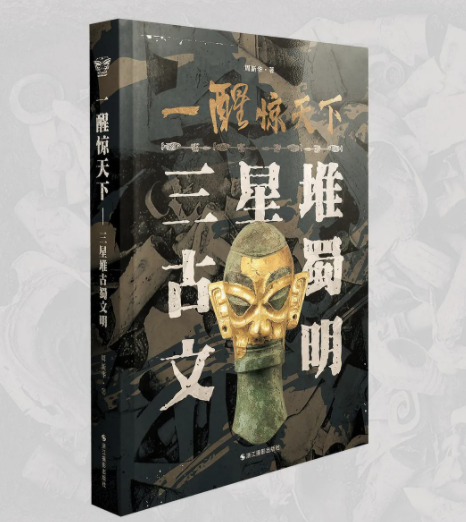
《一醒惊天下》,作者:周新华,出版:浙江摄影出版社2021年6月。